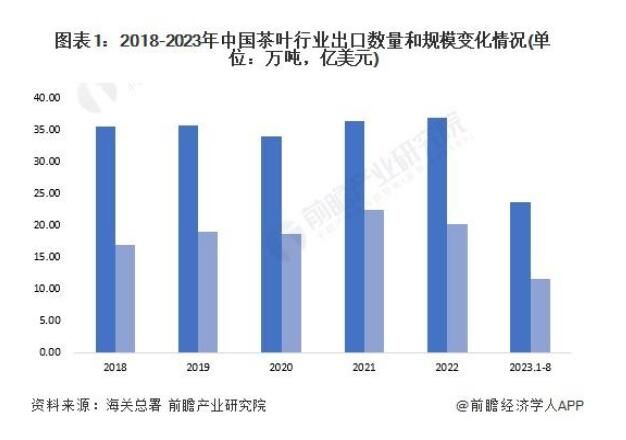以茶为前言,纵贯人生天地的大路。(图片起原:材料图片)师问新到:“曾到其间么?”曰:“曾到。”师曰:“饮茶去。”又问僧,僧曰:“未曾到。”师曰:“饮茶去。”后院主问曰:“为何曾到也云饮茶去,未曾到也云饮茶去?”师召院主,主应喏。师曰:“饮茶去。”这是《五灯会元》中纪录的闻名禅家公案,在人们讨论“茶禅

以茶为前言,纵贯人生天地的大路。(图片起原:材料图片)
师问新到:“曾到其间么?”曰:“曾到。”师曰:“饮茶去。”又问僧,僧曰:“未曾到。”师曰:“饮茶去。”后院主问曰:“为何曾到也云饮茶去,未曾到也云饮茶去?”师召院主,主应喏。师曰:“饮茶去。”
这是《五灯会元》中纪录的闻名禅家公案,在人们讨论“茶禅一味”的时分每每被提到。这里的“师”即唐朝闻名的赵州禅师从谂。这个公案是啥意义?我没法说!公案是学禅的人用来“参”的,不是用来说的,启齿即错,因此我不启齿!
禅师之意不在茶,禅家公案无迹可循,咱们来说说有迹的。
茶道茶道,技进乎道矣!以茶为前言,纵贯人生天地的大路,这是茶人的极致寻求!
前段时间看到央视《茶,一片树叶的段子》中阐扬的日本茶道景象,排场远大,尊严庄严。但是我觉得,更能由茶事而通向人生天地大路的,或是千利休的草庵茶。
当人们放下各种思考,直面当下的自我、当下的天下时,很靠近道。千利休的茶道,寻求的即是让介入茶道的人直面这种当下实在的天下。
在千利休以前和以后,日本茶人都在寻求各种珍贵的茶器,以茶器的珍贵水平和数目来掂量一个茶人的造诣。但千利休却鲜明不介意这些,他随时在通常生存中发掘少许一般的器物,把它们极妥贴地应用到茶事中。这种对通常器物的正视,我即明白为“回到当下的实在”。故意义的是,经千利休发掘应用过的一般器物,以后都成了茶道中的珍贵器物。
千利休很紧张的行动即是把举办茶事场所收缩到极致!这是极端伶俐的做法!经历这种极端的空间约束,迫使列入茶事的人不得不直面当下实在的本人和实在的天下,从而靠近道。
设想一下,宾主之间,云云逼近,来不得半点遮盖、做作,不得不回到实在的自我,不得不与对方身心融会,与茶、与身外的全部,实在相处、相融。有一点点私心杂念,都大概会造成出错;而一个细小的不对,都大概会造成全部茶事的失利。这对主客的请求都很高的,列入如许的茶事的人,通常都是经由当真起劲甚至艰辛的修炼的,并非普一般通的人,说“放下”就能做到的。但是在茶事的历程中,又是辣么纯真、纯洁!这是一种何等使人神往的茶事!《茶,一片树叶的段子》中那句俏丽的话,用来形貌这种茶事很适宜:“在明知不完善的性命中,也能够或许感觉到完善,哪怕,惟有一杯茶的时间。”
相对于日本茶道这种极致体验来说,中国人品茗相对安逸随便。而安逸的中国古代士人也一样能以茶为前言而通往道的地步。卢仝所刻画的“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,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即是这种地步。而卢仝是如何到达的呢?“柴门反关无俗客,纱帽笼头自煎吃”,他是一片面吃的茶;“一碗喉吻润,二碗破孤闷”,他是渐进的,刚首先喝与一般人差未几;“三碗搜枯肠,惟有笔墨五千卷”,好了,作为一个有常识的文人,他思路万千,并且能够或许把这种思路味同嚼蜡地表白出来;“四碗发轻汗,一生不服事,尽向毛孔散”,放下了,放下了,平与不服之事,皆云消雾散,能够说,他面临着当下真确本人、实在的天下了!卢仝的诗,向咱们活泼形貌了一其中国士人“以茶为前言,纵贯人生天地的大路”的历程。
陈继儒在《岩幽栖事》中说:“品茶,一人得神,二人得趣,三人得味。”一人,才是中国士人品茗的很高地步。日本茶人是经历缔造一个极致的情况来迫使人们直面当下的实在;而中国茶人,则是在奔放之中,独与天地精力来往。但两者都是“技进乎道”的地步,都是有迹可循、可说的茶道,有别于“茶禅一味”。